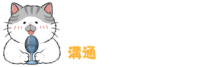About
賴彤兒(TonyLai)
我當過行銷顧問、創業家、工程師
現在正在前往作家與商業顧問的路上
兜兜轉轉十幾年,驀然回首才發現自己最喜歡的就是:
將縈繞在我腦中的各式想法抽絲剝繭,並釐清事物的本質
每個人都會有不同的際遇,不論是好的壞的,事後的感觸與經驗都將構築出每個人的獨特人格。我認為理解每個人的重大經歷,是認識一個人最深刻的方法,所以,讓我來分享一個影響我最深的經驗吧。
初生之犢不畏虎
我一直都是個資優生,這樣簡單的詞語就能概括整個讀書的年紀;國小國中名列前茅、高中讀台中一中、大學上台灣大學,即便有些青少年的困擾,但始終是小打小鬧的事件,不曾掀起過生活的浪花。上了大學以後,我接觸到了投資市場,一種華爾街精英式的慾望在心中蔓延,自然而然地就開始研究程式交易、閱讀投資經典、擔任證券投資社團的主要幹部,透過不斷地回測與優化,我找到了自己心中的「交易聖杯」,於是跟自己哥哥借了一筆不小的錢,打算靠外匯期貨市場創造自己的財富。
鋪陳到此有點電影的味道了吧,我猜想當時自己也是以主角這樣的角色看待世界的吧!但好的劇本總得有反轉才讓人印象深刻,現在已萬事俱備:一個沒經過檢驗的交易邏輯、一筆借來投資的資金、最重要的是一個過度自信的大學生。
人們總天真地以為重大的事件發生前,會有可以預測的跡象,那不過是事後諸葛自我安慰的想法;我遇到的東風,可沒半點預兆。
自動交易程序已經跑了一個月,最初幾天那種誠惶誠恐的心情已經平復,每天資產變動的狀況並不劇烈(大約在 2~3% 漲跌幅),整體來看即便沒有迅速致富,似乎也不會出什麼大問題。
「如果只是這樣該有多好」這是我後來很長一段時間的妄想。我還記得例常性打開帳戶看到虧損數值時的那種震撼,更準確地說是我仍能在回憶時感覺到當時的情緒:多種複雜且負面的想法一股腦地出現,讓感官喪失對實感的認知,耳中的聲音有種屏蔽感,可能是因為砰砰的心跳聲太大了;身體異常的寒冷,因為不管冷氣開多強,汗也不曾停過;腦部像當機一樣,只能任由不好的想法在腦中浮現。「我得逃離這一切」這是人的生物本能,「我得面對這個問題」這是我的理智,我沒有做到在第一時間停損,這對一個涉世未深的大學生來說要求高了點。
從意識到這一切發生後,我斷斷續續洗了很多次澡,希望能透過淋浴恢復清醒、更希望能從噩夢中驚醒。有很多次當冷水流過我的腦袋時,忽然有種「這應該不是真的,可能看錯了」的感覺,讓我甚至沒有擦拭身體就衝回電腦前,不過螢幕是冰冷的,正如現實一樣;我也試著撥通哥哥的電話,希望他能安慰我並且告訴我接下來該怎麼辦,但我沒有實行這個想法的勇氣。這些無意義的行為浪費了我一小時,也讓虧損進一步擴大,我已經不記得最後下了什麼樣的決心才讓我停損脫離市場,我猜想是虧損數值大到了我真的無力承擔的程度,才徹底壓垮了我的僥倖。
天會照常亮,雞排一樣香
回過神來已是三天後,說來好笑,我第一次體會到的斷片經歷,居然不是依靠喝酒達成的,更有趣的是,讓我恢復理智的僅僅是一片派克雞排。台大門口的雞排店,就在我每天上下課的必經之路上,我不記得自己出於什麼理由(可能是單純路過)才買了雞排當晚餐;但那塊雞排給我的感動仍然歷歷在目,它讓我深刻意識到:不論發生了我認為多嚴峻的事情,雞排的味道沒有改變,世界沒有改變,天還是照常亮,而我也還是照常會醒,那些我自以為天塌下來的大事件,只不是這個世界小小的漣漪,甚至連插曲都稱不上。不是遭遇困住了我,是我的思想困住了我!
這是我最接近道家所說的「頓悟」的一次體驗,這個體驗大概持續了幾個月,一種彷彿把思想霧霾吹散的感受,我清晰地看到了自己思想上的瑕疵、誤將各種信條視為理性的缺陷、自以為處在世界中心的傲氣、社會框架對我的束縛、被刻意地或粗糙地歸納的假真理。我重新認識了我自己;我重構了對世界的認知。
我相信有好幾個月的時間,自己處於行屍走肉的狀態,那是因為大腦無法確定哪些事該相信,正在重新思考所有曾相信過的事情,想必善於批判的個性也是在當時形塑而成的吧。
我思,故我在
如果讓我詳述反思的內容,那可能得另外開十萬字以上的文案,在這裡我就略過那些在操作上的瑕疵議題,例如:重視程式交易勝過交易邏輯本身的本末倒置、不理解過往數據無法推演未來的無知、過度優化產生的交易瑕疵、保持僥倖心態導致的止損不及時、借錢投資承擔了不正確的風險等等,這些議題有機會再說,這裡我們聚焦在更抽象、更基礎的思維框架上。
主角的錯覺,沒聽過的背景旋律
歸功於我的「人生勝利組」經歷,很長的一段時間,我的確有種自以為主角的大頭病,這讓我失去了發覺客觀世界與同理他人的能力,巨大的打擊當頭棒喝,雖然有點痛苦,但總歸是清醒許多了。沒有人是主角,在宏觀的角度上,我們其實沒那麼重要,「每個人都有其使命」只是教科書洗腦式的思想,根本不存在例證與根基。事實是,多數人終其一生,都只能對極少人產生意義,而且不一定是正向的意義。天真的期待自己是主角,希望世界以自己希望的方向前進,是無知且狂妄的。
實際上人類是透過第一人稱建立起對世界的認識,所謂的經驗不過是從接收外在的資訊並且內化的過程,我們根本無法肯定接收資訊屬於客觀的事實(唯心論的主題)、也無法肯定每個人的內化邏輯是同一套。換句話說,每個人都帶著某種偏見在看待世界,沒有例外。既然如此,怎麼可能會有單一主旋律的狀況發生?
想通了這點以後,反倒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,根本沒多少人關注我、在意我,我又何必有種偶像包袱,做自己想做的,承擔自己選擇的,這種隨遇而安的態度給生活帶來了新的氣象。另一個有趣的延伸思考是:如果每個人都必然帶有某種偏見,那這世界的歧異根本不可能消除(客觀上做不到),剩下的和平道路其實只有同理,理解每個人都不同(對事物的觀點),同時也理解每個人都一樣(都只是稱起世界運作的小螺絲),那些無意義的爭執才有消停的一天。
普洛克拉斯提之床

普洛克拉斯提之床(The bed of Procrustes)源自於希臘神話,傳聞某個古老旅店老闆名為 Procrustes,總會熱情邀請旅行者,並以豐盛的晚餐試圖挽留人們過夜,但在旅行者放鬆警惕入睡時,Procrustes 會把比床更高的旅人雙腿截短,把身長太矮的旅人身體拉長,其原因僅僅是想要讓旅人能完全符合床的大小⋯⋯
改變人的身長以遷就床是荒謬且不可思議的,但這種荒誕的事情卻不斷發生在我們身上,我們無端地接受了大量的固化思想,極少提出爭議與反對,儼然是種羊群心態。我們忘了每個人有不同的經歷、身處不同的位置、觀看不同的視角,如何能用相同的認知來面對問題?只因為散漫就放棄思考,那是對人生的不尊重,而且是對人類的迫害。
無知比邪惡更危險,實際上這世界的重大罪行大多不是出於惡意,而是無知與盲從造成的,不論是環境破壞、種族迫害、生物滅絕等等,很少事件是出於人類的本意,更多是因為缺乏思考的盲從導致的悲劇。個人的選擇亦是如此,我就是很好的例子,我絕不是因為想要虧損才投資,實際上就是因為無知才犯錯。也正因如此,我花了大量時間重構過往沒有被驗證的一切認知、重新懷疑所有人想要強加在我身上的信仰、任何無理由的社會框架。我會用盡一切力量試圖掙脫普洛克拉斯提之床。
懷疑一切信仰,包含這句話本身。但也要小心別掉入懷疑論者的弔詭思維當中,懷疑是一種「工具」而不是「目標」,我們透過懷疑保持高度理性,拒絕粗糙而籠統的接納既定觀點,並不代表我們要成為否定一切的討厭鬼,不相信跟反對仍然有巨大的差別。例如:以理性思考的角度來說,我們當然要懷疑神佛的存在,但這並不表示我們需要跟虔誠的教徒起衝突。認知上或許可以很超然,不過人畢竟是群體動物,把求真外顯成行為,那只是一種白目,並不是真理,對於他人的信仰,我們大可以換個思路:不考慮信仰的真實性,而考量信仰的價值,也就是說信神佛對此人帶來何種益處、對群體帶來何種益處。
從消極的人生產生積極的態度
最終,所有抽象的反思都會流向「空」(某種形而上的虛無感),因為探究本源是無窮盡的,終會挖光可思考的根基。這種空虛的認知,常伴隨著消極的態度面世,例如:探究金錢的本源,會發現價值不過是人類共識而成的,如果連人生都還沒被定義,其上的價值又有何意義?類似這樣的想法不斷湧出,在認知上將脫離社會框架,偏離人們口中所說的積極人生(因為值得積極的事物都將被否定)。
很久以後我才發現這個疑問的另一個角度,那就是思想所脫離的是社會上的要求與框架,也就是既定而成的「積極」,並不是出於人本願的積極。就像是人生的三大問(我是誰、我從哪來、我要到哪去),社會對這些問題早有定見,但那些觀點真的是我們接受的嗎?正因為能夠消極地面對群體框架,才會對自我需求產生積極反饋;當我們屏蔽了社會要求的干擾,才會看到自己重視與追求的。破而後立,人生的問題就剩下選擇與承擔後果。
如何進行精明的選擇,那是技術問題。我心底最後的疙瘩就剩下反思後的空虛,如果一切皆無意義,那生活的價值何在?直到我發現其實大可把「不能接受空虛的狀態」,也視為一種結論而接受,亦即接受無理為理的一環;無為有的一種形式,認識到理性不過是人類用來接觸世界的工具,沒有任何方法能證明這個工具是完備的,反倒讓人釋懷。
至此,我完成了自己思想的底層建構,更多技術上細節問題我也會寫文章分別討論(也歡迎你留言告訴我想要看什麼內容)。很感謝你能閱讀到這裡,我沒有在這個頁面上照著習慣摘要生平,而是落落長的寫了一大堆,其實是故意,因為我仍有自己的傲氣:我認為沒有辦法耐著性子看完這些內容的人,沒有資格認識我。感謝你不是這樣的人,我相信我們可以成為朋友,這個網站有很多互動的方式,我很期待能與你交流。